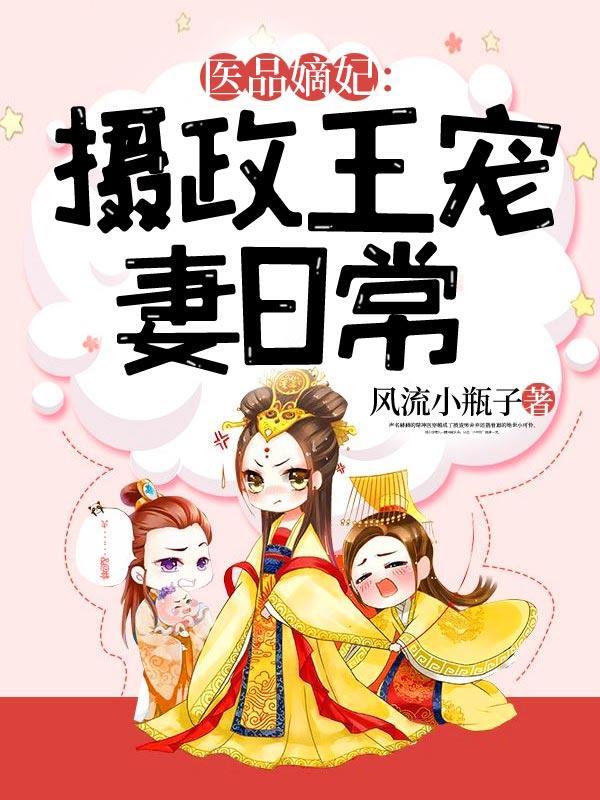藝術小說>木卿楚既明 > 第57頁(第1頁)
第57頁(第1頁)
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好答案,許衍不小心摳破了大拇指關節處的薄皮,有點疼,他“嘶”了一聲松開手,喝了口水,平靜地與渠星對視。過了很久,渠星終于動了動,他起身繞到寫字桌後:“讓我看看你的字。”筆墨紙硯都是現成的,許衍在桌前愣了半天,不知該寫什麼。他倒不是露怯,隻是考慮太多:渠星手下的功夫不必說,眼睛也甚毒,他寫讨巧的字讨不來巧,真寫不讨巧的,也就真不讨巧。渠星也看出他的躊躇,給毛筆潤了墨,強行塞進他掌心:“随便寫吧,我看看。”是支大楷毛筆,最常見、最常用、最常換的筆,非常熟悉。許衍腦袋一片空白,落下了第一個字。這支毛筆已經到了該淘汰的邊緣,筆尖有點秃,他寫第一筆時沒注意到,再加上落筆僵硬,第一個字寫得束手束腳,形太聚。第二個字好一些,他有意克服稍秃的筆尖,字終于有了些許露出的銳氣。說來也快,這些字就在心上,他寫過無數次,是孫景晤當年參加比賽的那幅字。隻是孫景晤寫的是隸,許衍寫的是行草。捱過和不熟悉硬件的摩擦,後邊的字越發流暢。他寫得舒适,字形也舒展開來,比前邊的字潇灑許多。寫至“又還是、春将半”時,一旁的小鹌鹑呂桃兒都忍不住低聲叫了聲“好”。尤其是那個“春”,上下都肆意到了極緻,但内裡仍有筋骨守着這個字。過了因為落筆舒适而起的狂放,行至最後幾個字,恣意逐漸被常年習字的約束取代。不比呂陶頌臨字時的拘束,許衍即使提起了“科班生”的身份,筆下的字依然不落窠臼。形從不是束縛字的原因,“曾許不負莺花願”寫得克制,卻也美。許衍把筆放好,退了一步,低頭看自己的字。每個寫字的人都有這樣的時候,寫時是一種心情,寫完的當下立刻再看心境又會不同。就是前幾分鐘落的墨,每一個比劃許衍都記得清楚,這一撇是怎麼寫的,那一捺又是因何格外出挑。他給渠星讓開地方,站到了一旁。自從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,渠星本人和書法更近了,但和書法圈以及寫書法的其他人自然而然就疏遠。他很久沒見過像許衍這樣年輕的習字者,看字時不自覺就仔細了些。許衍的字很漂亮,行草要寫到世俗意義上的漂亮門檻不算高,難得的是,他的字不是空有漂亮。很多寫字的人會陷入迷宮,看太多貼、臨太多字,自己手下的字難免因為見過名家而縮手縮腳。也有一種情況,和名家寫得太像,刻闆的像實在是沒有魂魄。渠星的手在墨迹未幹的草紙上比了一下,他很準,幾次停頓恰恰就在許衍心境、筆觸變化的地方,他轉過頭說:“你和你父親的字不太一樣。”“對。”許衍說,“他……他沒有親自教我,啟蒙是馬坤池老師。”渠星不可能認識三密籍籍無名的書法老師,随便點了點頭:“你們父子真有趣,當年我聽說你父親的隸數一數二,專門去看他,他不願給我寫,我空手而歸。過了幾個月,他又自己上門,說得了新字要給我看,就是你寫的這詞。”“字幾乎可以說跳出去了,沉穩大氣不說,細節處可見靈氣。”意識到渠星說的這幅字是爸爸參加比賽前、在更早時寫的初版,許衍屏住了呼吸:“然後呢?”“我想收藏,但他覺得不完美,不願留。我們争了好幾天,各自讓步,他在字上署了名,我落了日期——字确實是毀了。”看許衍頓時失望,渠星又說,“拍了照,也有掃描版。”說不上是什麼感受,許衍聽明白了,但又像過于明白反而發愣。他倒退一步,腳下一軟,扶住桌才沒狼狽跌倒:“您……您有……您是說,那幅字還在?”“我倒忘了問,是誰讓你來找我。”渠星在身後的資料櫃裡找到标注了“孫”的文件夾,将裡邊所有的資料全部倒在桌上,“這是我這兒有的,關于你父親的所有資料,如果我沒丢三落四,那幅字就在。”來之前,甚至是進入這扇門前,許衍一直說得輕松,如果有這幅字,他要鳴炮三天以示慶祝。可現在,字就在眼前,他卻連翻一翻的勇氣都沒有了。他揪住呂陶頌的衣服,聲音顫得厲害:“師、師兄,你給我找、找找。”呂陶頌輕快地應了一聲,把他的視線堵在身後,手下極快地把資料攤開,幾乎是一眼就看到了那幅字。他也激動,罵了句髒話,把照片從紙堆裡抽出來:“2007年4月,是比賽前吧?沒錯吧?”“比賽那幅字是8月重寫的。”許衍擠到桌旁,不敢去奪那張照片,湊着腦袋去看,“是4月嗎?你看清了嗎?”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重生發小+番外 [崩鐵]論如何作為姐姐養大砂金 寒冬末世,但我幸運拉滿 [崩鐵]怒罵老闆後被對面選成令使了 辣麼大個神之子去哪了 再問仙途[女配] 東方不敗之君子滿樓+番外 讓他降落+番外 謀奪帝心 下山退婚卻被女總裁帶去領證 農門小甜妻 全家都是近戰武士,除了我 寵你,十年未改 [原神]撿個散兵帶回家 将軍女扮男裝後,與她成婚了 我的動機是你+番外 被自己創造的AI病态監禁 刺客甲+番外 掰彎就跑?沒門+番外 公主的品格[系統]